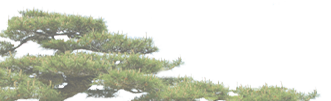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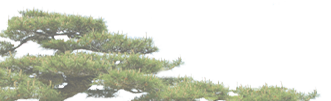

王煥淼 中國地市州盟報新聞攝影研究會理事、學術委員,湖南省攝影家協會會員,湖南省地市州報新聞攝影研究會秘書長,常德日報社記者
華國鋒同志逝世了。曾和他相處近一整天的我多少有些傷感,雖請田雄幫我在網上留有“華老,您一路走好!”的唁言,仍感意猶未盡,特寫下這篇文字,敬獻給中國的第一老實好人!
我國最權威的新聞媒體----新華社發出通稿:“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曾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的華國鋒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時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華國鋒是新中國成立到今天,所有最高領導人中,任職年紀最小(55歲)的一位,也是中共歷史上結束大規模政治斗爭的第一人。新華社的通稿,無疑傳達了黨中央對華國鋒同志的歷史定位。
我作為一個曾在1970年隨華國鋒同志視察枝柳鐵路建設的隨行人員,聽到黨中央對華國鋒同志的這個歷史評價,感到十分欣慰。對歷史的態度,往往是檢驗一個政黨是否實事求是的重要標尺,因為歷史是人寫的。歷史告訴我們,為了某種特定的需要人為地歪曲歷史的情況,在世界歷史上屢見不鮮。歷史還告訴我們,凡是不尊重歷史的人,終究會被歷史所拋棄;凡是尊重歷史的人,則永遠得到歷史的肯定,進而永遠得到人民的愛戴。黨中央對華國鋒同志從1976年到1981年擔任黨、政、軍最高領導人期間卓著功勛的歷史評價,是我們黨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精神的生動體現,也進一步彰顯了我們黨更加成熟、更加開放的態勢。
往事如煙。那是38年前的1970年12月19日,我接到9230工程指揮部的電話,前往澧縣界嶺公社等候拍攝領導視察“三線”建設工地。料峭寒風中,我們在與湖北接壤的界溪河,迎來了時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華國鋒一行。華國鋒個頭很高,典型的北方漢子。他頭戴單軍帽,身著軍大衣,精神抖擻地來到修建枝柳鐵路的民工群中,和大家親切握手,噓寒問暖。
“文化大革命”那陣子,軍方特“吃香”。不僅從中央到各省都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實施“軍管”負主責,連地區、縣一級,也由駐軍或人民武裝部首長出任“三結合”革命委員會的主頭,我亦曾是解放軍的一員而被委以拍攝領導視察的重任。
當時與華國鋒同時到“三線”視察的省軍區政委卜占亞,只不過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省委書記。我的印象中,他根本就不把華國鋒這個中共中央正式委員、湖南省的“一把手”放在眼里。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我當時是由澧縣人民武裝部直接調遣去的唯一一名攝影者。行前,政委關致和、副政委苗慶盛千叮嚀萬囑咐,一定要拍好領導難得到縣、鄉里視察的鏡頭。那時候,別說現在的數碼相機,連用眼晴直接瞄、拍的135單反相機也沒有,只有一臺上海產海鷗牌的120雙鏡頭反光照相機。每拍一張,必須放在胸前,低頭調焦,上弦,按快門,扭卷片器,如此循環,拍完12張,再換膠卷。條件雖不好,但我還是想竭盡全力拍到華國鋒和卜占亞在一起會見群眾的照片。可是,卜占亞這位老兄的所作所為,讓我根本就沒有這個機會—他壓根兒就不與華國鋒走一道!按常理,作為候補中委、省委書記,應該謙讓中委、第一書記先行,而在界溪河,我們首先見到的卻是八面威風的卜占亞。待他率領的大隊人馬浩浩蕩蕩過去之后,我又匆匆忙忙返身去拍后到的華國鋒會見群眾的照片。
那時不像現在,領導視察后還專門在會議室聽匯報、作指示。當時只見卜占亞一個人侃侃而談、滔滔不絕,身邊圍滿了人群,熱鬧非凡;而華國鋒第一書記只有幾個人陪坐在火坑邊,寂靜冷清,也沒聽到他發表什么指示,更聽不到他“侃大山”。我那時對華國鋒最深的印象就是:這位書記慈眉善目,為人忠厚老實,簡直就像個農民。“馬善逗人騎,人善受人欺”的民諺當時就從我的腦海里跳出來,只是不敢說。后來華國鋒出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我還私下與要好的朋友談起過這個印象。
午飯在指揮部—稻草棚內舉行,華國鋒和我們在大食堂吃同樣的膳食。沒有致辭,更沒有音樂,只聽碗筷碰撞之聲。我永遠記得這樣一個鏡頭:華國鋒吃完第一碗飯,自己持碗來到飯盆邊。“怎么沒人添飯?”鄰桌的我實在看不下去,“不要說他是領導是客人,就憑年齡,我們年輕人也應該幫他裝裝飯呀!”那年我25歲,憑著軍人的快捷,速去為華國鋒同志裝飯。華國鋒連說“自己來,自己來。”堅決不讓我裝,我倆還捧著飯碗相持了一會,最后他取得了“勝利”,還不忘說聲“謝謝你。”我當時的想法就是不能冷落了老實人。
視察活動完成之后,清一色的吉普車隊浩浩蕩蕩開往縣誠,那時也不見“鳴鑼開道”的警車,只出現了我至今不忘的一幕----車隊進縣城時,全城停了電。冬夜伸手不見五指,只有一路車燈。進縣招待所后,燈光復明。這大約是澧縣革命委員會為保證首長安全,采取的嚴格保衛措施吧?!■
(該文摘自常德史志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