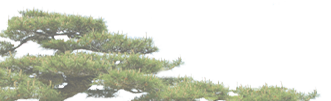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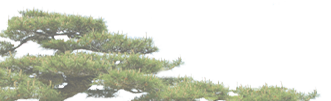

【作者介紹】 黃一兵,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
【正 文】
1977年3月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有各省區市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是粉碎“四人幫”后召開的第一次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總結了粉碎“四人幫”以來的工作,討論并通過國家計劃委員會提出的《關于一九七七年國民經濟計劃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過去普遍認為,這次會議為全黨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撥亂反正,為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設置了障礙。客觀地說,這次會議雖然在總的指導思想上堅持并貫徹了“兩個凡是”,但是,會議第一次較為系統地提出了“走向大治”的基本方針;重新肯定了1975年全面整頓工作所取得的成績,正式宣布恢復并接續1975年全面整頓時期的措施和做法;對當時一些引起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給予明確回答。實際上,1977年的中央工作會議是在較為寬松的環境中召開的,會議取得了一些積極成果,特別是一些與會者在討論中提出的新觀點和新主張,對后來形勢的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
『一、國民經濟調整方針的提出和否定』
粉碎“四人幫”后,中國社會發展處于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這個歷史階段作了這樣的界定:形成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所謂“徘徊中前進”是指“黨的工作”狀況,但它對中國社會發展產生了影響,形成了一段具有過渡性質的發展時期。這種影響主要表現為:第一,囿于“兩個凡是”的束縛,中國社會還難以“根據國際國內條件的變化和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江澤民:《在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3年12月27日)確立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第二,粉碎“四人幫”后,中國社會的整體形勢沒有倒退,在局部領域還有所前進。1977年的中央工作會議就是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召開的,具有“徘徊中前進”的顯著特點。
1977年中央工作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和決定國民經濟發展的近期規劃和目標,而對這個議題展開討論必然要涉及怎樣認識和把握當前經濟形勢問題。客觀地分析當時的經濟形勢,可以鮮明地看到主要受到兩種相互交織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一是長期以來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障礙經過“文化大革命”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二是粉碎“四人幫”后國民經濟較為快速的恢復性增長。盡管對后一種因素,當時可能感受更直接一些,但是從1977年中央工作會議前后情況看,中央對這兩種情況都有所認識。還在1976年12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華國鋒就代表黨中央提出了“1977年應是走向大治的一年”。普遍認為,“大治”目標的提出與“一個新的躍進形勢”的形成是直接相關的。但實際情況是,在1977年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后,中央對如何“走向大治”的戰略思考經歷了一段發展過程,曾有過對國民經濟進行實事求是/調整”,然后在新的基礎上發展的設想。
粉碎“四人幫”后,黨中央重新提出了“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的口號,強調“打倒了‘四人幫’,我們要以極大的努力,加快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打好關鍵十年這一仗,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國家計劃委員會:《關于一九七七年國民經濟計劃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重新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斗目標很重要,它表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總方向重新回到了正確的軌道。在1976年底、1977年初重新提出上述奮斗目標的時候,實際上是作為一個長期發展目標提出來的,按照當時的設想,它是一個至少需要十年基礎性建設的發展目標。而對于實現這個奮斗目標的開局之年的1977年,中央有關部門明確提出,國民經濟要經歷一個調整時期,以便為后來的發展打下基礎。1977年初,國家計劃委員會在醞釀制定《關于一九七七年國民經濟計劃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時就提出:“一九七七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做好這一年的工作,使國民經濟扎扎實實地前進一步,就可以為第五個五年計劃后三年大發展做好準備。由于-四人幫.的干擾破壞,當前國民經濟中的一些比例關系不很協調。有些問題,需要在調整長遠規劃時研究解決。有些問題,在一九七七年計劃中,就要認真著手解決。”(國家計劃委員會:《關于一九七七年國民經濟計劃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為此,針對當時國民經濟發展中突出的農業和輕工業不適應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問題;工業生產中燃料、動力和原料短缺問題;基本建設規模過大過長問題,國家計委提出了一條先調整穩住陣腳再前進發展的方案,并著手對197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做出調整。應該說,國家計委的這個方案是較為冷靜和客觀的,它比較清楚地認識到國民經濟發展中實際存在的困難和制約發展的種種因素。
對于國家計委提出的在調整的基礎上發展國民經濟的設想,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在最初的討論和聽取意見的過程中,盡管也強調要多看有利形勢,但對于把“調整”作為國民經濟的“主旋律”都表達了理解甚至認同的態度。華國鋒在聽取國家計委的匯報中指出:研究國民經濟計劃,從現在看,困難大一些。報告中反映的情況很清楚了。今年基本建設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除了已經達成的協議外,都要壓縮。這樣會給安排上帶來一些困難,但如果建成了項目沒有煤、沒有電,還不是停在那里?要壓縮科室人員、非生產人員,壓縮的決心可以再大一些。工業如此,農業也如此。即將召開的計劃會議既要鼓勁,也要留有余地。(華國鋒在討論《關于一九七七年國民經濟計劃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過程中的講話(1977年2月15日))李先念在聽取意見的過程中也強調:不要完全根據生產指標算財政,你增長多少,我增長多少,把虧損扭轉過來就是大數字(李先念在討論5關于一九七七年國民經濟計劃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6過程中的講話(1977年2月15日))。
從1976年12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始,中央在國家發展規劃上作了一些規模宏大的部署,這些部署主要是一些中長期規劃和部署。但是從1977年初的情況看,中央對于國家短近期發展目標,開始有了更加實際和更加符合國家發展狀況的考慮。
然而,就在討論《關于一九七七年國民經濟計劃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的過程中,1977年第一季度國民經濟形勢有了很大好轉。根據國務院有關部門統計,從3月份開始,工業生產、交通運輸、商品購銷、財政收入全面上升,并且相繼超過了歷史同期最好水平(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關于今年上半年工業生產情況的報告》(1977年7月30日))。這種情況的出現,影響了正在討論中的對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在對國家計委提出的《關于一九七七年國民經濟計劃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修改稿的討論中,有同志提出:可以回想一下,1974年“批林批孔”,“四人幫”搗亂,生產下降,1975年3月抓起,形勢很快好轉。那時“四人幫”還在,現在“四人幫”揪出來了,形勢不同了,可以想象比1975年會好得更快一些。許多同志甚至很樂觀地認為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
在這樣的氛圍中,在討論國民經濟是否需要先調整再發展時,更多的人主張在這個問題上要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在新的形勢下,不單獨提出調整任務比較適宜,這樣有利于鼓足干勁繼續前進。因此,華國鋒在討論《關于一九七七年國民經濟計劃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最終修訂稿的總結講話中指出:今年有調整的意思在里面。但考慮來考慮去,沒有提調整,今年經過努力,要前進一步,而且為今后三年更好地完成五年計劃打基礎。一說調整,好像五年計劃又要調整了。還要積極一點。在指導思想上,首先要看到目前存在的困難。不看到,采取不承認主義不對。要看到困難,但也不要把困難看得過重了。(華國鋒在討論5關于一九七七年國民經濟計劃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6過程中的講話(1977年3月1日))
討論《關于一九七七年國民經濟計劃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的最終結果是“調整”的設想被放棄了,而“積極前進”的方案得以確立。由于《關于一九七七年國民經濟計劃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是1977年中央工作會議準備討論通過的主要文件,因此,會議在規劃“大治之年”的基本方略時,“積極前進”成了主基調。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代表黨中央所作的主題講話中專門談到了“當前社會主義最有利條件”的問題。他說,粉碎“四人幫”以后,蘊藏在廣大干部和群眾中被壓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得到了發揮,這是我們搞好經濟建設和其他社會主義事業的最主要、最根本的有利條件。這個有利條件越往后越能顯示出它的巨大威力。(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77年3月14日))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華國鋒系統闡述了“走向大治”的方略,著重談了“八個一定要”,即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幫”的斗爭進行到底,把他們顛倒了的路線是非糾正過來;一定要把我們的黨從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整頓建設好;一定要把我們黨的各級領導班子建設好;一定要落實毛主席關于“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一定要堅持毛主席指引的方向,繼續開展教育、文藝和科技革命,堅持貫徹“雙百”方針;一定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一定要發揚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統籌兼顧,全面安排。這“八個一定要”在后來召開的黨的十一大上被概括為“我們黨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抓綱治國的八項任務”,成為當時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準則。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將這次會議有關“八個一定要”思想的闡述與黨的十一大有關“八項任務”的闡述進行比較可以看出,中央工作會議在強調“積極前進”指導方針的同時,依然關注了對“前進基礎”和“現實狀況”的認識和把握。中央工作會議在闡述應當怎樣估計當前經濟上遇到的困難以及怎樣對待這些困難的時候指出:“四人幫”的干擾、破壞,確實給我們帶來了許多困難,這些困難所造成的后果,已經逐漸暴露出來,應當向群眾說清楚,克服困難,要有一個過程。我們要盡一切努力縮短這個過程。會議上,李先念在談到加快經濟發展時,特別強調了國民經濟發展中各有關方面存在的薄弱環節。關于農業問題,在肯定農業生產成績的同時,他指出“我國的糧食生產還是低水平的”;關于市場問題,他強調了“現在有些地方,忽視了多種經營,忽視了經濟作物,這個問題值得注意”;關于外貿問題,他強調“要把生意做活”,尤其需要加強香港、澳門地區貿易。在談到如何發揮中央和地方兩種積極性的時候,他說,在總結過去教訓的基礎上,要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主動性,一定不能再搞“條條專政”,要堅持適當放寬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決不能走回頭路,等等。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表明,在缺乏對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正確總結的情況下,一味強調“積極前進”的方針,容易導致具體工作中脫離實際追求高速度、高指標情況的出現。1977年中央工作會議以后的形勢發展也再次證明這一點。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從這個時期中央對國民經濟發展規劃的討論和決策過程來看,最終出現了“一個新的躍進形勢”是多種因素參與形成的結果,也是逐步發展而形成的一個結果。(未完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