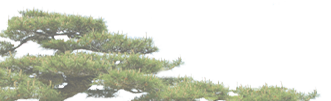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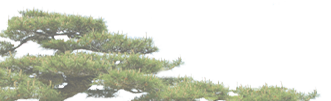


【作者介紹】 楊宏雨,男,1965年生,江蘇淮安人,1996年在華東師范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化問題研究。
周瑞瑞,1986年生,浙江溫州人,2016年在復旦大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現為上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后研究人員,主要從事中共黨史、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研究。
【正 文】
『一、十一大召開的歷史背景』
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離世,中國出現了巨大的權力真空,江青等人借機加緊搶班奪權。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聯手擊敗“四人幫”。10月8日至15日,又采取果斷措施,粉碎了“四人幫”的余黨在上海策動暴亂的計劃。18日,中共中央將《關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通知》印發各級黨組織。1976年12月10日、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全國印發了《“四人幫”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之二,全國掀起了揭批“四人幫”,清查其余黨和幫派體系的運動。經過揭、批、查,“1977年上半年前后,全國各地的武斗動亂被制止了,出現了安定團結的局面。”
粉碎“四人幫”,中國從天下大亂走向天下大治,這是十一大召開的第一個歷史前提。
幾乎在粉碎“四人幫”的同時,華國鋒等人已經在醞釀糾正毛澤東晚年親自安排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錯誤。據吳德回憶,1976年10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提出解決鄧小平復出問題的三條方針:第一條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第三條是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接著在1977年1月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提出:“小平同志不是一個人,是一層人。”“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應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1977年3月,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表示:“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華國鋒在鄧小平復出問題上的方略包含了二個考慮:(1)全局性:水到渠成,不影響穩定;(2)合法性:經過正當的程序和正式的手續。
按照上述方略,粉碎“四人幫”之初,中央在強調深入揭批“四人幫”的同時,“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10月26日以后,根據華國鋒的指示,改為“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其實“繼續批鄧”也好,“連帶批鄧”也罷,總體上只是一句虛的口號。筆者檢索了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幫”消息以后的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社論,除了10月25日的“兩報一刊”社論有“繼續批鄧”的字樣外,其余的一篇也沒有。 1976年底,華國鋒在審閱元旦社論時,親自刪掉了“批鄧”的文字。1977年1月,《人民日報》上提及“批鄧”二字的文章“僅3篇,2月以后絕跡” 。
華國鋒等人一邊淡化、消解“批鄧”,一邊積極為鄧小平復出做準備。1977年3月,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宣布:“經過調查,鄧小平同志根本沒有插手天安門事件”;“‘四人幫’對鄧小平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都應當推倒。”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了鄧小平于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寫給華國鋒等人的兩封信。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鄧小平1976年4月以前的職務。
在著手讓鄧小平復出的同時,華國鋒等人還為1976年4月的天安門事件進行事實上的平反。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發布第23號文件指出:“凡純屬反對‘四人幫’的人,已經拘捕的,應予釋放;已經立案的,應予銷案;正在審查的,解除審查;已經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釋放;給予黨籍團籍處分的,應予撤消。”文件雖然也說:“凡不是純屬反對‘四人幫’,而有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絕不允許翻案。”但文件強調的是前者,使實際操作者能夠利用空擋,施展變通的智慧。1977年3月,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當時去天安門廣場的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是悼念周總理的,其中許多人是對‘四人幫’不滿的,反對的。”這樣天安門廣場事件在性質上變成了群眾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活動。這就為釋放因參與天安門廣場事件而被捕的人提供了正當理由。在此背景下,北京和各地都抓緊平反工作。從1976年11月到1977年7月,北京市已將天安門事件中被拘捕的300多人全部予以釋放。
鄧小平的復出和天安門廣場事件的基本解決,使中國有了一個比較清明的政治環境,有了一個可以預見的政治走向,這是十一大召開的政治前提。
粉碎“四人幫”以后,面對百孔千瘡的中國經濟,華國鋒等人接過鄧小平1975年整頓的方略,狠抓國民經濟的治理。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華國鋒在講話中把會議的宗旨確定為“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并強調“我們各方面的工作都要貫徹執行這個基本方針。”他還使用了1975年整頓時期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中“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的論斷,強調發展經濟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意義:“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之一。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的前提下,生產發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盡管講話中的不少話語仍有“文革”剛結束時所特有的意識形態特征,但新話語的出現以及對“發展生產”的高度關注,猶如絲絲涼雨滋潤著干涸的中國大地。1977年4月,華國鋒利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的機會,發揮毛澤東的有關思想,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關系的某些環節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需要加以改革的情形是經常會發生的;上層建筑的某些環節不能保護甚至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需要加以改革的情形也是經常會發生的。說社會主義制度有優越性,并不是說,在人類社會中普遍存在的這些基本矛盾已經消失,而是說,能夠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主動積極地解決這些矛盾。”“我們必須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盡快地發展生產,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逐步得到滿足,才能使社會主義制度獲得愈來愈充分的物質基礎。”不難看出,華國鋒已經提出了“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一命題。此外,從上述熟悉的話語中,我們不難看到中共“八大”報告中正確思想的影子。華國鋒還用1975年《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中的有關思想正面闡發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工人階級自己的宏大的技術干部隊伍,宏大的知識分子隊伍是不行的。” 1977年5月,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召開,華國鋒在會議上除了闡發了前面我們已經提及的一些積極思想外,還特別指出:“革命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迅速發展生產力,實行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
在承接鄧小平1975年整頓有關思想的同時,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通過的《關于一九七七年國民經濟計劃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肯定了1975年的全面整頓是堅持了“毛主席革命路線”,領導整頓的干部是“堅決執行毛主席指示的領導干部”,從而事實上已經“從政治上肯定了1975年整頓的方向和路線” 。1977年6—7月間,《人民日報》刊登專文,全面肯定指導1975年整頓工作的三份文件,反駁“四人幫”橫行時期稱其為“三株大毒草”的污蔑 。
鄧小平1975年整頓的功績現在已被國內學者普遍接受,有作者認為“1975年整頓是對‘文化大革命’撥亂反正的開始”;“是改革開放的試驗”;“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二次偉大轉折的前奏”。 眾所周知,鄧小平的整頓只進行了幾個月,就因毛澤東的反對而夭折,而粉碎“四人幫”后由華國鋒等人接續起的治理工作不僅沒有中斷,而且直接啟動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更大更全面的改革。但對華國鋒主政的這兩年,不少黨史著述稱之為“徘徊的兩年”,否定之聲不斷。兩相比對,不免讓人有厚此薄彼之感。
從粉碎“四人幫”起,作為中國式政治動員的一種方式,提前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口號就頻頻出現在當時的報刊中;各種與經濟工作相關的全國性會議紛紛召開,重要的有1976年12月的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1977年1月的全國煤炭工業學大慶趕開灤會議、全國輕工業學大慶座談會,2月的全國鐵路工作會議、全國基本建設會議,3月的全國計劃會議、全國林業水產會議、全國冶金工業會議、全國財政金融學大寨會議,4—5月的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6月的全國三夏生產會議、全國棉花生產會議,7月的全國地質部門工業學大慶會議、中國科學院工作會議、全國外貿部門學大慶學大寨經驗交流會、全國郵電學大慶會議、全國農田基本建設會議,8月的全國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全國糧油工作會議。由此可以看出,經濟工作事實上已經開始成為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
由于黨中央的重視和全國人民的努力,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形成的空前有利的社會環境下,中國國民經濟從文革時期的停滯、徘徊、下降轉為穩定上升。1977年“工業總產值3月份以來逐月增加,上半年完成全年計劃的48%。鐵路平均日裝車,4月份達到55100車,超過歷史最高水平,6月份達到57000車。80種主要工業產品,5、6月份的產量,絕大多數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其中26種創造了歷史最高月產水平。29個省、市、自治區的工業總產值,有24個上半年超過了上年同期水平。6月份,所有的省、市、自治區都比5月份增長,有23個達到和超過了歷史最高月產水平。”
國家工作重點的轉向和國民經濟的全面好轉,是十一大召開的經濟前提。
談及十一大,就不能回避“兩個凡是”的問題。“兩個凡是”的核心是如何看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而這又不能不涉及到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對于“兩個凡是”的來龍去脈,韓鋼在其文章中作了全面的說明,筆者結合韓鋼的文章,提出幾點看法:(1)“兩個凡是”的主旨是為了維護毛澤東的地位和形象,堵住國內外各種“非毛化”的議論,防止這些議論導致國內局勢的動蕩。(2)“兩個凡是”的提出不是為了阻止鄧小平的復出和對冤假錯案的平反。如前所述,鄧的復出在剛粉碎“四人幫”時就定下來了,為老干部落實政策的工作也一直在進行,但客觀上對平反冤假錯案有一定的阻礙。(3)“兩個凡是”代表了當時黨內相當一批人的認識水平——1977年2月7日社論的起草者就是國內著名理論工作者、黨史問題專家,是一個認識問題,說明“人們對粉碎‘四人幫’以后工作上和其他一些問題的認識,有一個過程” 。(4)提出“兩個凡是”和維護、堅持“兩個凡是”之間不能劃等號。華國鋒等人一方面提“兩個凡是”,另一方面又準備鄧小平復出,肯定鄧小平1975年的整頓,并恢復了文革前的許多正確做法,事實上是在否定文革。這種“打‘左’燈往‘右’轉” 的做法,雖然在理論上和邏輯上有許多問題,但在過渡時期,卻不失為一種比較穩妥的策略。(5)“兩個凡是”并不是要堅持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特別是在文革中所犯的錯誤。比如在為配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發行而發表的文章中,華國鋒雖然用《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作為標題,但眾所周知,毛選第五卷的內容起于1949年,終于1957年,與“文革”沒有什么關系,涉及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思想也少之又少,因而整個文章并不是要堅持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特別是文革的錯誤理論,而是希望通過正面闡述建國初期毛澤東比較正確的理論來為撥亂反正提供依據。(6)“兩個凡是”是因為不知道如何引導人們正確認識文革、正確看待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而采取的一種比較簡單、粗暴的辦法。在當時,如何看待文革,如何在否定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的同時又能維護好毛澤東的旗幟,這是全黨面臨的一個難題。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對于文化大革命,也應當歷史地、科學地、實事求是地去看待它……但是不應匆忙地進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共中央花了2年多的時間,經過5600多人的討論,形成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和毛澤東的晚年才做出一個政治結論。但即使如此,黨史專家王長江認為,這個決議在今天看來還有很多缺陷和不足。換言之,在剛粉碎“四人幫”的具體歷史條件下,要徹底否定文革和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是做不到的。(7)在鄧小平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要用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之后,華國鋒等人及時改正了錯誤。“1977年4月以后,華國鋒再未提過‘兩個凡是’,而黨內文件、國內媒體也不再出現‘兩個凡是’。” 當時鄧小平尚未復出,華國鋒是黨內最高領袖,這種知錯就改、從善如流的態度是難能可貴的。1977年8月的十一大政治報告采納鄧小平的意見,使用了“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體系”這一話語。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時,在中共中央發布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中稱毛澤東是“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敬愛的偉大領袖、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偉大導師”;粉碎“四人幫”后不久,華國鋒一面強調高舉毛主席的旗幟,一面將這一過分的調子降下來,改為“偉大領袖和導師”、“我們黨、我們軍隊和我們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 。在如何高舉和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問題上,盡管黨內曾有“兩個凡是”的錯誤提法,但很快就得到了糾正 。1977年3月,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文革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是一個黨內大多數人都能接受的評價。1977年4月,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表示“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和工作的部署”,強調要“世世代代地高舉和捍衛”毛澤東的旗幟,信中沒有觸及“文革”問題。1977年7月,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也肯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各方面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表明在華國鋒主政期間,寬容、諒解是中央高層的一種常態。
粉碎“四人幫”后,中共高層領導之間同舟共濟、團結一致,以大局為重、事業為先,和而不同、求同存異、擱置爭議的做法,使各種不同意見能在若干問題上盡快達成妥協。這是十一大順利召開的一個重要歷史前提。(未完轉下一篇)
(該文摘自《哈爾濱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14年第2期)